在永新县禾川镇袍田村的犹狮岭自然村,村后有座缓缓隆起的小山坡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坡上静静矗立着一所小学——胜利小学。它在我记忆中的存在,恰似坡间那些倔强生长的松树,不知何时扎下根须,却早已与山峦共生,成为一道沉默而深情的风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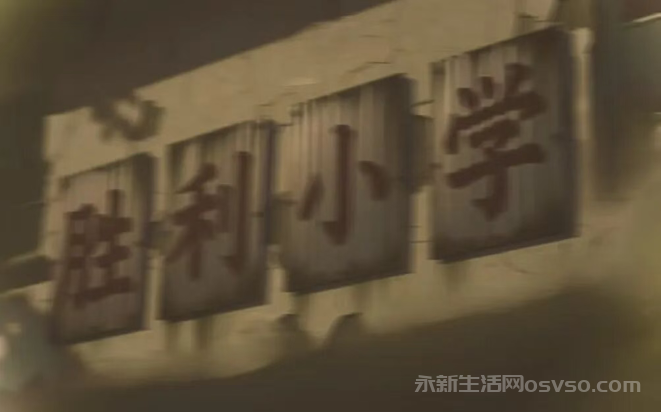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所只收本村与邻近孩童的村小。它朴素得近乎坦荡:没有围墙,更没校门,唯有那依坡而建的教学楼与大礼堂,天为幕、地为席,山川是它无边的庭院。所谓“校门”,只是四块锈迹斑斑的铁皮钉在斑驳的墙面上,上面用红漆刷着“胜利小学”四个字。
那红色被岁月洗刷成浅粉,却因漆料厚重,始终不肯完全褪去。走进这扇象征性的门,学校的全貌便沿着山坡次第展开。它的布局层次分明。进校须先上一段缓坡,坡顶是几间教室,算作第一层;拐弯再上一段土坡,便到第二层——两层之间根本没有楼梯,山坡本身就是最天然的阶梯。上下课的讯号,是挂在楼顶的一口铁钟,系着长绳,值班老师一拉,清亮的钟声便如透明的波浪荡开,穿透山野,惊起麻雀,也唤回孩童漫游天外的思绪。钟声每日指引着我们,奔向那些洒满光斑的教室。
每一年级仅两个班,每班约四十人。教室是灰瓦二层小楼,墙色斑驳,木窗上嵌着三五块玻璃,其余的窟窿用油纸糊住。冬天的寒风从缝隙钻入,在教室里回旋低吟;夏日的蝉声也由此泻进,与读书声交织成独特的合唱。课桌是长条原木,早已裸露,上面重叠了无数届学生的刻痕与墨迹——细细辨去,有歪扭的姓名、稚拙的小人、杂乱的算式。
男女同桌的课桌上,深深浅浅的“三八线”刻下了最纯真的界限。这一切,俨然一部无字的年谱,在坑洼之间记录岁月的流转。教室里的学习生活简单而纯粹, 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主课。没有五花八门的教辅,一切知识都凝缩于课本之中。最难忘是考试时节——老师亲自在蜡纸上刻版,用油印机一张张印出试卷。
考前,老师抱着一叠散发浓烈墨香的试卷进教室,那气味清冽又朦胧,瞬间占领整个空间。我们小心传递这些犹带湿润的试卷,生怕蹭糊字迹。考完后,每人手上都沾满薄薄的黑墨,这浅浅的印记沉淀在时光里,成了永远也擦不去的、关于奋斗的“胎记”。严格的制度为这份纯粹增添了份量。 两门主课不及格便要留级;若只一门稍差,还可于开学前补考。每逢暑假将尽,总有几人提前返校,在空荡教室中伏案疾书。窗外是家长焦灼的身影,窗内是紧皱的眉头,构成九月前夕特有的风景。正是这严格的制度,让我们自幼懂得:学习需要一颗敬畏之心。然而,真正令我们心驰神往的,总是钟声响起后的世界。一放学,我们便挣脱了黑板与粉笔的束缚,奔向那流淌的渠水、神秘的洞穴与无边的田野。学校前面的那条约三米宽的北干渠道,是我们夏日最大的诱惑。
渠水清可见底,深度刚没孩童胸膛,成了天然泳池。每逢午后,总有三五孩子脱得只剩短裤,扑通跳进水中。那是个还没有“防溺水”概念的年代,亲水是孩童天性。老师虽常叮嘱注意安全,却也默许了这份炎夏难得的快乐。当时没有标准的体育场,但快乐从不稀缺。 女生多是玩跳皮筋、抛石子。她们三五成群,在教室前空地上画出方格,或念着童谣跳跃翻飞,或蹲在地上专注地抛拾石子,指尖翻动间尽是天真烂漫。校园的边界之外,还藏着更大的冒险乐园。
旁边的防空洞黑黢黢的洞口仿佛大地的神秘眼眸。孩子们无一不爱钻洞探险,猫腰进去,被阴湿的土气包裹,又怕又兴奋。洞中回荡惊叫与欢笑,手电光柱在黑暗中划动,仿佛要刺破一切未知。我们的童年,也与脚下的土地紧密相连。 那时的袍田垄还是纯粹的农村,田野广袤,稻浪连绵。农忙时节,学校会放农忙假,让农家孩子回家帮忙。
金黄稻田间,俯身收割的身影如浪中浮舟,空气里弥漫稻香与汗水的咸味。虽然我们年龄小,却深知农事艰辛,便以拾穗、晒谷、送水这些稚嫩的方式,为家人分担。时代的车轮终将向前。 九十年代初,“希望工程”的春风吹来,胜利小学迎来了真正的蜕变。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崭新的教学楼,学校也随之更名为永新县希望小学。这座新校舍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的校门和高高的围墙。校舍虽新,根脉未改,它依然矗立在那片山坡上,聆听同样的松涛。后来,为纪念贺子珍前辈,县里决定在希望小学的基础上,异地新建一所学校,并命名为“子珍小学”。新校舍坐落于原址对面的开阔地上,与坡上的老校区遥遥相望。
而那片坡地,它的故事还在继续。 原址后来的角色几经转变,从飘荡着奶油味的职校,到回响着读书声的进修学校,这片土地见证了教育从传授技艺到培育师者的不同形态。眼下,教育的根须又一次深深扎回这里。 因子珍小学新校区教室不足,这片土地再次回归本真:十余个班级的孩子重返此地求学。校门口又贴上了“子珍小学希望校区”的牌子。童声书韵又一次成为主旋律,宛若一个温暖的轮回。近些年我曾去过几次。希望小学时期的教学楼还依然屹立。
北干渠道流水潺潺如昨,只是再无水中嬉戏的孩童;防空洞一带树木繁茂,也再无人钻洞探险。我独立坡上,忽一阵风过,松涛如诉,恍惚间又听见当年的钟声——清亮如昔,穿透时光。那所没有围墙的学校,其实早有围墙:一边是贫瘠的物质,一边是丰盈的精神。而我们这些钻洞的孩子、戏水的少年,钻的何尝不是时间的洞?爬出来时,便把童年永远留在了洞口的另一头。
唯余钟声飘荡,成为永恒的记忆坐标。现如今,虽然校名更易,用途几改,但琅琅书声从未断绝。孩子们坐在历经风雨的教室里,或许不知这个地方曾经所有的故事,但阳光依旧照在他们的课桌上,山风依旧轻抚他们的脸庞。犹狮岭上的松树依然苍翠,坡上的野花依然年年开放。那口铁钟或许早已不知所踪,但它的声音却烙印在每一个曾在此求学的人心里。
每当夜深人静,闭上双眼,那钟声便穿越时空,再次响起——清越、悠长,召唤我们回到那个无墙的校园,回到那个贫瘠却丰饶的年代。站在山坡上,我望着这片历经轮回却始终孕育希望的土地,悄然离去。身后,读书声正朗朗响起,与记忆中的钟声交织合鸣,奏出一曲跨越时空的乐章——那钟声从未远去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继续回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。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