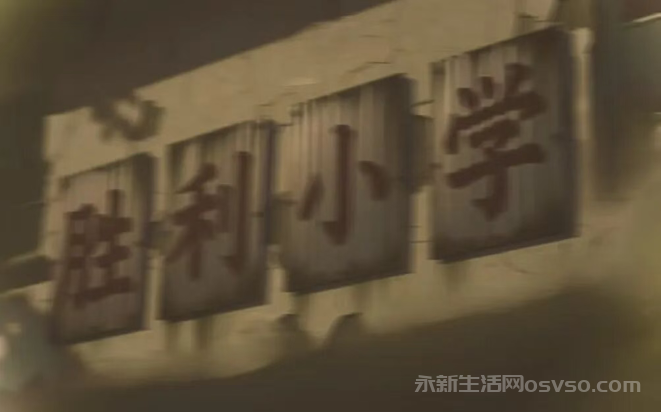“永新城西袍陂有水,汀泓清碧,名曰忠义潭。”
——(清)贺怡孙《忠义潭记》
对一个潭的描述,语言往往是难以抵达的。我一次又一次地靠近它,却总是很难将我的感受复述给别人听。
上个周末,我沿着禾水河畔缓行,再一次来到城西郊外的袍陂。水波声像风一样向我扑面而来。禾水,又称永新江,《方舆纪要》记载:“源出禾山,亦曰禾江。”它是赣江一级支流。禾水一路奔泻而下,在江西永新城西被一道高高的堤坝拦腰而断,水于此停下了急促的脚步,变得安静起来,形成了一个宽阔幽深的水潭。
一个潭的名字来历总是藉由一段经历或者传奇。许多年前,一顶北宋的轿子停在城西的河边。由此发生了一个“刘沆挂袍”的故事。故事有趣,但又很庄重。

刘沆,庐陵第一人,与欧阳修是同科进士。彼时,刘沆在湖南做官,回乡省亲,路经永新城西。那年逢大旱,老百姓深受其苦,刘沆见父老乡亲正在号子声声里筑坝拦水,感念百姓用水之苦,即刻下轿,解下官袍挂于树枝,他望了望那风中招展的朱红色官袍,喊了一句“水不到田,袍不取回”,便毅然投入搬石挑土之中。之后,他还向朝廷打了报告,要了款项,让这项水利工程第一次进入了朝廷的视野。高高的堤坝将奔腾的禾水阻断。村民感念刘沆心系家乡的事迹,将河坝取名“袍陂”,潭水灌溉的那片农田取名“袍田”。从此,在一条河的润泽下,这个僻静的县城享受着绵长的富庶和安宁。
时间来到南宋。距刘沆挂袍已经过去200多年了。此时,南宋的江山风雨飘摇。元兵长驱直入,直指南宋都城临安。可叹的是,“王令已寂寞,匣中剑空鸣”,朝中大臣几乎无人敢站出来,主和的占多数。右丞相文天祥,是为数不多的主战派,他誓死抗元,匡复大宋。在文天祥的领导下,江西的抗元军事行动如火如荼。
江西永新的知县彭震龙(文天祥的妹夫)响应文天祥的号召,举起抗元的大旗。彼时,“文天祥”三个字就是一种精神、一种号召,在彭震龙的麾下,自然就是在文丞相的麾下。彭震龙奔走呼号,联络张、萧、段、谭、刘等八姓豪杰,组成一支义军,并于县境西部义冈设立据点。张姓是永新的大姓,有“过了浮桥十里张”之称。曾为学士院检阅文字的张履翁,召集永新张姓全族,歃血为盟:“我们都是大宋人!报国捐躯,义不容辞,就是诛十族也要血战到底!”舍家报国,誓言铿锵。曾为文天祥幕客的从事郎萧焘夫兄弟,召集了萧姓全族人马响应勤王。其他各姓,也一起响应,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抗元义军。队伍声势浩大,八姓健儿势如怒涛排壑。很快,一举收复了永新县城。元军仓皇逃离,城头的帅旗,被女人扯碎做了小孩的尿布。
失败的元军自然不罢休,准备反攻。增援的元兵也越来越多,且来势凶猛,很快县城被围得像铁桶似的,哪怕一只鸟都飞不出去。彭震龙站在城头,拔剑在手,怒目厉声喝问八姓豪杰:“势至此,怎么办?”
众答:“一团血!”言辞简短,但大义凛然,豪气干云。
此时,元兵已迫修门外,他们在城外喊话:“降元者,赏纹银一百两。”然而,这种诱惑对于这支义军毫不奏效。那时,人心就是一座坚固的城,回答元军的是乱雨般的箭弩,是愤怒的炮石。
“若不降元,城破之日,草木不留。”失去了耐心的元军厉声威胁。
彭震龙自始衣不解带,枕戈待旦,他对着八姓豪杰发誓:“人在城在,人亡城破。”他带领大伙杀将出去,一时间铁马交鸣,杀声震天,血飞如雨。彭震龙、张履翁等,皆身负重伤,血染衣衫,却依然奋勇杀敌,一次一次地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。
可悲的是,堡垒最终从内部被攻破了。“邑叛贼,宋制使刘盘降元,引兵袭境,城遂陷。”
南宋将领刘盘贪生怕死,变节降元。战争形势一下就发生了变化。彭震龙的义军被动挨打,他只能寄希望于文天祥的救援,可久候援军不至,最后弹尽粮绝。1277年7月19日,城陷,元军冲入城内,开始屠城。彭震龙也不幸被捕,但是面对威逼利诱,他浩然正气,誓不降元,最后被腰斩于市……文天祥听闻此事十分敬佩,也深感悲恸,写下《挽彭司令震龙》一诗:“堂上会亲戚,可怜马上郎;呻吟更流血,干戈浩茫茫。”
混战中,谭姓中的谭宗祥与其弟谭文贵突出重围,携妇孺老幼三千余人,从西门且战且退,打算回到义冈集合休整,却在城西五里皂旗山至袍陂渡口的峡谷中,被元军围困。由于地形险要,加之袍陂无桥,前无去路,后有追兵,三千余人很快陷入了绝境。众寡已然悬殊,突围全无可能。“宁为大宋之鬼,不为敌酋之奴。”义军无一人愿屈膝投降,遂个个身绑巨石沉潭,从容赴死。谁也不曾想到刘沆曾经极力修建的袍陂,几百年后成了一支抗元义军的殉道场。一时间,风狂树摇,水涌石怒,在场的元兵都被震得步步后退……
当地民众听说后,纷纷赶来悼念,呼喊着他们熟悉的名字,可是禾水呜咽,山风猎猎……“若夫八姓三千人者不过山陬穷民,聚族执戈,以抗强元,至于抱石沉潭,不遗苗。”史册里文字记载是如此吝啬,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浓缩为一行小字。
“水而纪,此忠义所由,名也,鸣乎忠。”后人为纪念这为国而死的三千义士,在他们殉难处竖起一座石碑,上刻“忠义潭”三个大字,还修建了一座忠义祠,立八姓豪杰神主牌位,以此祭拜。
“苍苍义山,汤汤义潭。是兴烈士,义胆忠肝。”一支义军,以家殉社稷的气节在浩瀚的史册里倔强地留下印记,也为后人树立了一道忠义爱国的丰碑。《宋史》说,从古亡国不止一宋,未闻有以黔首三千人同死社稷者。确实,三千义军同时投潭壮烈殉国,在历史上从未有过。七百多年后,我站在袍陂的水涘,思绪如麻。禾水汤汤,日夜不息。江风一遍遍地吹着,将往事吹得很远很远。
(作者:曾亮文)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